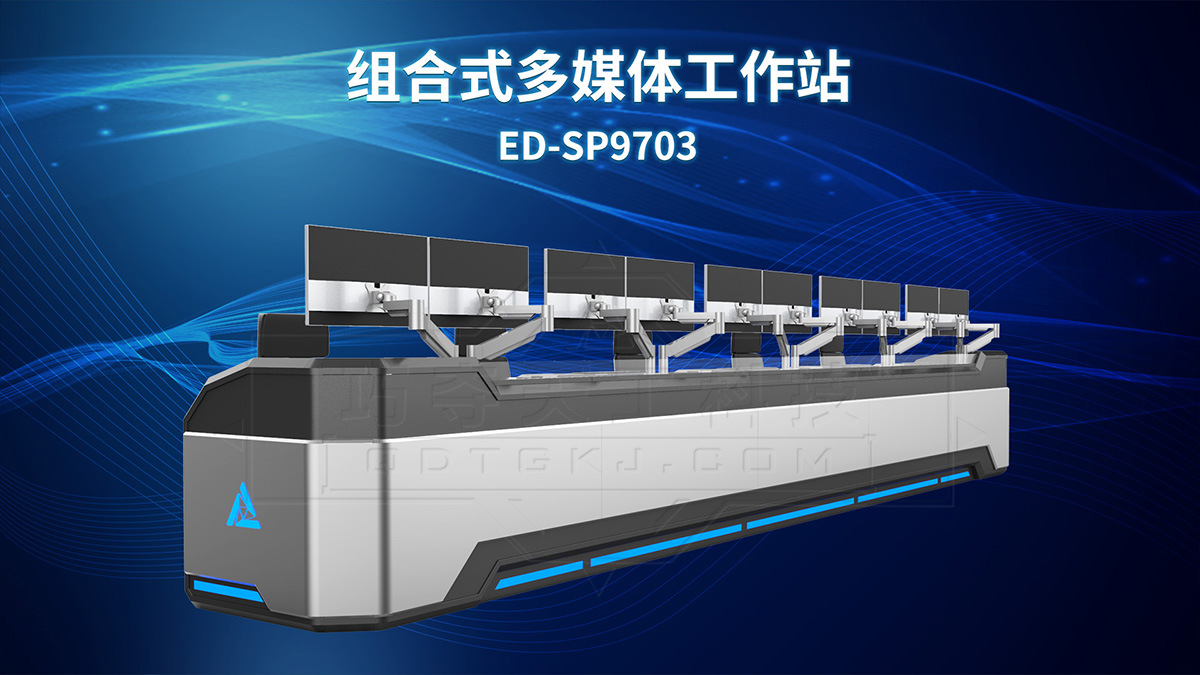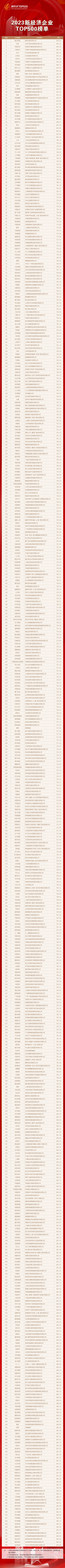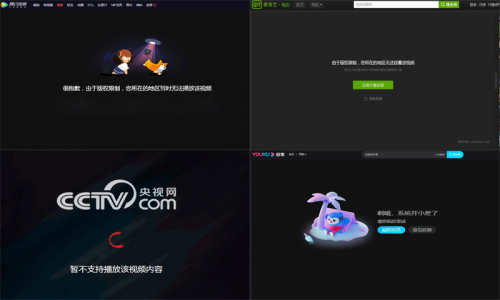电视剧《繁花》开播前,我们在东一美术馆见到了它的原著小说作者金宇澄,由他的200多幅画作组成的展览“繁花”正在这里展出。
表厂钳工、文学编辑、作家、画画的人……和金宇澄的聊天开始不久后,我们很快忘了这些身份,掉进他说的一个又一个故事里。我们刚落座时,阳光打在窗外的黄浦江上,晃得人分心。再注意到窗外时,太阳已经落山,而我们浸在金宇澄的故事里,觉得江面金光粼粼不过是几分钟前的事。
《文化先锋》第三期,我们记下了金宇澄讲的那些故事。
智族GQ:为什么《繁花》的故事只能发生在上海?
金宇澄:资料记载,1836年,有两艘英国船开去广州,那里几千年来都是乡绅阶级统治,大地主没发话,底下人不敢动,不让船靠岸,结果有人说,你们去上海试试看。船开去上海,当时还没开埠,老城厢里面就有很多人过来围观、搭讪:
你们来干嘛?船上装了什么东西?我们可以来参观吗?要不要到我们老城厢来借房子住?特别地好奇,特别地友好,因为当时上海老城厢也没有几年历史,四乡八野的临时人员都在这里。
上海就像一个大森林,每个人在里面都可以找一块地方生活,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自由自在的市民文化。这就导致开埠以后,晚清鸳鸯蝴蝶派的包天笑在回忆录都写,那个时候苏州的大家子弟,全跑到上海去,因为老头子们管不着。而这都是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了。
人是最讨厌别人管的,我自个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,就这么简单对吧?就像张爱玲说的,在乡下,我多买半斤腊肉,邻居都知道,但在城里,我当着窗户前面换衣服也没人看见。所以年轻人都游到这个城市来。
智族GQ:但也有人不喜欢上海,认为市民文化的另一面是精明、市侩、甚至挟带着一些不近人情的冷漠。
金宇澄:那一定是会有,你比如沈从文当年最有钱的时候搬到上海来,上海多爱他啊,给他出了三十几本书。结果他去找裁缝做大褂,跟人家赊账,裁缝说,谁知道你是谁啊?你去把这个大褂拿去当铺当掉,把我的工钱结掉。
所以沈从文就很讨厌这种商业社会,很无情,不像北京有一种乡土温暖的气息,你赊账,掌柜就会给你记上,但同时它也会牵涉你的自由。
智族GQ:最近关于上海的另一件热闹事,莫过于《繁花》被改编成电视剧以后再次引起的各种讨论,而您一直以来对于这些讨论的回应都是“不响”,为什么?
金宇澄:开始写《繁花》也是在网上连载,那个时候风气不像现在这么会骂人。关于争议,我从文学的角度来讲,我们从五四之后就开始搞批判现实主义,等于说在对社会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批判了。我们没有经历过生活怎么发生就怎么写,所谓自然主义的这个阶段。
我记得自然主义的代表左拉,有篇小说有趣,很简单,就说姐姐和妹妹是两种人,姐姐一辈子就希望找一个小公务员,生俩孩子,就这么过一辈子,妹妹呢,从一开始就觉得她要进入上流社会,每个月都月光,还问姐姐借钱打扮穿衣服。到了结尾,妹妹果然嫁给了一个老贵族,就像童话一样。但你换成批评现实主义就肯定是把妹妹批一顿。
讲到《繁花》上,就像我一个北方的作家朋友说,看了你这个《繁花》,你们上海人什么男男女女怎么这么黏糊,我们北方,男女关系,行就行,不行就拉倒。批了上海半天,但是后面结尾一句话最好玩,最后说,我也想到上海来生活(笑)。
智族GQ:往往就是这种矛盾之处才显得人可爱。
金宇澄:回到实际生活中,人都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,都是暧昧模糊的。所以现在各种评价,好人坏人,色狼渣男或什么,我认为真正的小说,根本没办法几个词解释,根本是混在一块的东西,但在每个人物身上又很合理,它需要有这种尴尬。
所以《繁花》里面说,做人多少尴尬。
智族GQ:怎么理解这种尴尬?
金宇澄:我自己对人生的感悟,人活着的时候,一切都是立体的,可触摸,可感受,声光电,但一旦死掉,立马压扁了,没有了。
不要说我们个人,整个时代也是一样,你还在分什么八零后、九零后、几零后,五百年在历史书上面就一页纸啊。
所以在活着的时候,我们要充分地了解,尝遍各种味道,到一定年龄回看过去,有时候想自己怎么这么可笑。但是偏偏不断有一些说漂亮话的小朋友出来,支撑了一种吵闹的风气,因为他们最愿意说话。真正懂的人都不吭气的,就是不响了。不是没想法,他都知道,只是闷声不响而已。
智族GQ:但据我们观察,似乎表达欲这件事在年轻人中正在形成一种两极化的趋势,一些人声音越喊越大,另一些人就越来越倾向于沉默。
金宇澄:我一直说现在的年轻人是中国历朝历代知道事情最多的这么一代人,现在只要有一个手机,人生被细化的程度是过去不能比的,但同时压力也特别地细化。
智族GQ:在您看来,知道的多,是一件好事吗?
金宇澄:我不说别人,我就说说自己。
我现在上网看抖音,有时候也看得停不下来。我们过去一代人,哪怕再知书达理,都不会知道那么多细节,无论是从制造业、养殖业,包括种花、堆麦秸垛、马蹄铁是怎么换蹄,包罗万象,太丰富了,你就是大百科全书都不如,都比不上现场给你看。
我最佩服的一个中年人,他在山里用当地的原料做各种传统的手工艺品。比如过去女人化妆用的一种香油,他把猪油熬出来浇在一个方盒子里,凝固后一颗一颗茉莉花摆满在上面,等花都枯萎了,再来一批新的,直到最后这块油已经满含了茉莉花的香味,最后再加入别的东西做成一小块香膏。各种各样这样的名堂,过去《天工开物》里面也没有,对于我这个民工出身的人来说,真的是获益匪浅。
智族GQ:难以想象金先生抱着手机刷短视频停不下来的画面。
金宇澄:所以我说,传统“读书”的时代,实际上已经过去了。
智族GQ:但不论时代如何发展,新的介质如何涌现,书都还是很重要的吧?
金宇澄:文字、图像或者声音,都是创作,重要的是创作,我对创作的理解就是保存,就是要把我眼前这几平方米的所有东西,详详细细地把它保存下来。比如你说,没有那些通俗的明清世情小说,我们怎么知道当时老百姓是这么一个情况?
我写《繁花》也就是写我面前这几平方米,上海就是一个亚马逊的热带雨林,我根本不了解它,我只能看清我面前有一些什么植物,如果远方有一个黑影经过,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大象或是一头巨兽。
所以我经常鼓励别人去写作,每个人保存自己的那一小块,就像我鼓励陈冲去给《上海文学》写专栏,她和她哥哥在80年代前后是非常文艺的一对兄妹,这么一个上海的生活场景在小说里还没表现过,给我一种填补空白的感觉。
起初是有一回我跟她说,你老家的房子现在被人租出去做私房菜,弄得挺时髦,她说哎呀我们家门口一块空地现在盖了楼,不能看了,但是又念念不忘讲了很多她过去小时候的事情,我说你可以写出来,在我们《上海文学》发嘛,后来她把家里的人,外婆、祖父、哥哥一点一点写起来,写了三篇以后,就不用催了,现在都要出单行本了。
智族GQ:这也是您在《繁花》之后就开始转向非虚构创作的一个原因吗?因为真实历史里随意抖落出来的细节,都可以像扇到人脸上的耳光那样痛。
金宇澄:我记得陈冲专栏写到她外婆,她外婆在抗战阶段千辛万苦接孩子(陈冲母亲)从上海回四川,有个细节特别难忘,在过日本人关卡的时候,外婆在旅行包里放一个皮球,如果有检查,她就把旅行袋打开,一个皮球滚出来,小孩就去追那个皮球转移视线。陈冲就问说,外婆如果还是不让你过怎么办呢?她外婆就说,我随便。
这个话就特别震撼人,让我想起美国一个伊朗裔的女作家写过一个长篇,叫《信仰大道上的月光》,也是写一个女人千辛万苦从伊朗跑到美国,第二天全家赶来看她,发现这个女人已经变成一个大胖子,把整个房子给堵住了,人根本出不来了。实际意思是她一路太辛苦,故事太多了以至于膨胀了。
智族GQ:那么在您看来,对于这一代年轻人而言,尤其是对于还有创作欲和表达欲的年轻人而言,这个年代还可以靠写作留住什么呢?
金宇澄:十多年前,我在《南方周末》看到一篇文章,报道福建有个小村子,从清朝开始祖祖辈辈就都是往外走的,到世界各地去,没有一个年轻人待在镇子上。外地的小姑娘、小伙子都到这个小渔村来伺侯老人、开店,打牌都是用外币的。
哎呦,我一看这个我就心里想说,我如果是个小青年,就到那个小渔村去生活,学当地的方言,一个一个故事记下来,我可以出砖头这么厚一本书。开会的时候,我就跟那些年轻作者讲,你们干嘛不写这个呢?这个是财富。
结果过了两年,接到一个电话,说金老师,我是谁谁谁,我已经到了这个小渔村了,你不是有一回讲这个事情吗?我记下来了。我真的是蛮激动的那种感觉,我想我居然影响了一个人。
但真的挖到一个矿,也许也不是想象中那样好。这个作者已经有孩子了,她带着孩子跑到这个小渔村,引起了当地所有人的警惕,碰到了铁板,非虚构最后就成了虚构。
但写作就是这样,我们都是匆匆的过客,我们都留下一些东西,到底能不能保存也不知道,反正就是表示我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过,就是这样,来过一趟,就这意思。
转载:智族GQ
免责声明:市场有风险,选择需谨慎!此文仅供参考,不作买卖依据。